叶童回应机场被骂:爱是克制,最新热门解析实施_精英版121,127.13
- 43
- 2025-03-31 12:05:35
- 12
往期的文章中,讨论过调节愤怒的方式。但是“愤怒”作为一种情绪,我们有足够认识它吗?最近,小编在阅读蒂芬妮·史密斯的《情绪之中》发现,原来人类的每一种情感都有它的本质、历史、演化和表现方式。
今天,我们就好好认识一下“愤怒”......
双眼发出怒火,脸颊通红、嘴唇颤抖、肌肉鼓胀,蓄积了准备进行破坏的可怕冲动,连毛发都竖立起来……这个场景无疑可以用来描述班纳博士变身为“不可思议的浩克”时的景象。
事实上,这是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尼加(Seneca)对愤怒的描述,出现在现存最具影响力、最古老的“愤怒管理学”著作《论愤怒》之中,这本书成书于西元一世纪。
他认为愤怒是“所有情绪之中最可怕且最狂热者”,是一种“短暂的疯狂”。发怒者在愤怒时更近似野兽,而非文明的人类。
如同更早前的亚理斯多德所认为的,愤怒是感觉遭贬抑或受辱所导致的——特别是侮辱你的对象并没有足够的地位。尽管他承认愤怒这种情绪对战场上的战士有所助益,但若发生在罗马市集广场和宫殿廊道则毫无容身之处。在后者,愤怒只会造成分裂和瓦解:引发激烈的争吵,而且在随后爆发后悔的情绪。因此他建议,怒气一旦产生就该加以抑制,理性思考当下的情势。
愤怒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情绪类型,其中包括了沸腾的怨恨和赌气的成分、被惹恼所造成的脾气爆发,以及突发性的怒不可遏。愤怒者可能表现出令人害怕的冷静从容,或发狂般的激烈肢体反应。过度愤怒会破坏婚姻生活,害我们丢掉工作,或者替行动增添燃料,驱使我们更加努力。
或许有一点道理是亘古不变的,那就是对许多世纪以来论述愤怒的作者们而言,问题在于愤怒是应该被表达。“我希望你会生气,这样我们就能将怒气公开宣泄出来。”在伍迪·艾伦的电影《曼哈顿》中,戴安·基顿这么说道。伍迪·艾伦对此回应:“我不会生气的。我是说,我有把怒气藏在心底的倾向……我长了肿瘤作为替代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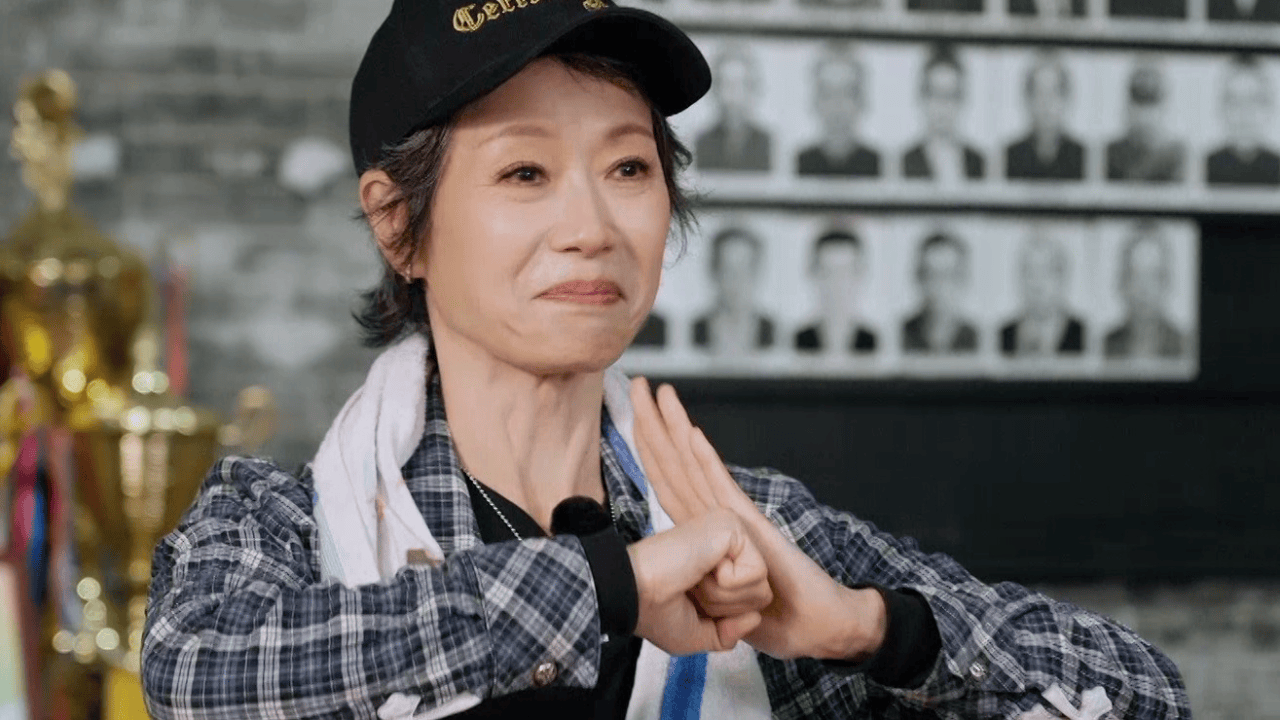
你可能认为表达愤怒有益健康。“发泄出来总比闷着好”并非当代的概念,某些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医生都热衷于替病患释放怒气。虽说愤怒会耗损生命元気,但有时也被认为是有益的。十一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·布特兰解释,由于愤怒将人体热能导向四肢末端,因此能使体弱和卧病在床的人恢复精力,他甚至认为愤怒可以治疗瘫痪。
“原始呐喊疗法”的诞生,以及精神学家连恩于1960年代晚期在英国金斯利馆成立的治疗社群,将愤怒的表达视为治疗过程中的大突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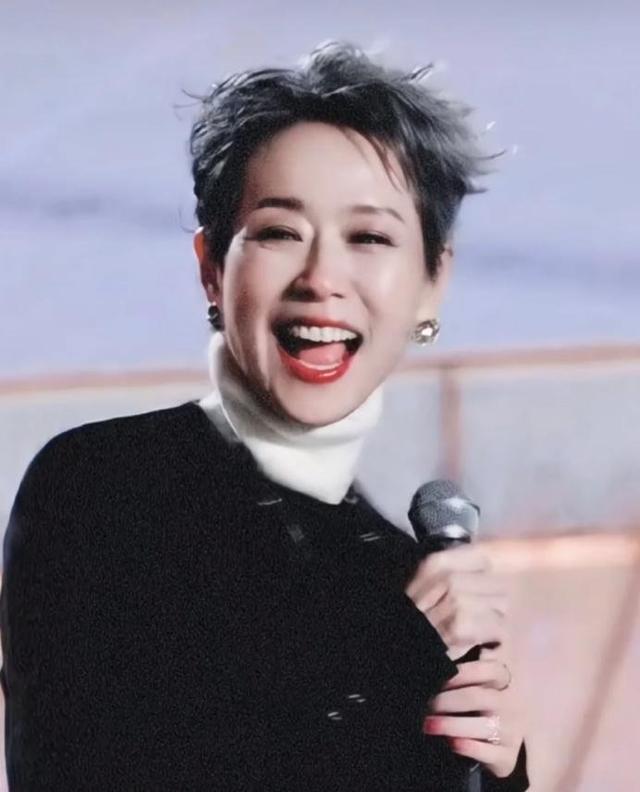
怒气的爆发被视为个人真实身份的展露,打破病人所建立的假我——以协助他们应付在不诚实世界中的生活。这些治疗者相信,暴怒能使病患重新与他们的真我连结,将病患从作为避难所的成瘾习惯和疯狂中释放出来。对某些人来说,这个办法的确奏效。
至于当今心理治疗师较感兴趣的,则是设法了解愤怒从何而来,以及为何需要愤怒来帮助我们应付生活,而非利用它激发宣泄作用,或是“真正地”展现怒气。
愤怒以奇特、出乎意料的方式爆发。当我们遭受批评或被不公平对待,在愤怒的刺激之下,我们会产生比平常更为强劲的反应力量。此外,大发雷霆也以其他方式使我们受益,它可以放松紧绷的肌肉,并且暂时镇压住其他令人不太舒适的情绪,例如恐惧或不值得的感觉。
愤怒的爆发也能帮助我们处理罪恶感:藉由将怒气宣泄在别人身上而转移了咎责,暂时让自己得到些许缓解。在这些情况下,愤怒似乎是“真实的”,不过精神分析学家表示,愤怒可能是一种假饵,也就是说,我们下意识比较偏好昙花一现的爆发怒气,而非察觉那些被遮掩的痛苦感。
因此,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谈到愤怒的表达时,争辩的重点已经再度转移。眼下的问题并非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健康而表达愤怒,而是被愤怒——无论咆哮张扬的暴怒或静静焖烧的怒火——所抑制的,究竟是哪些情绪。
- End -
文|摘自 蒂芬妮·史密斯的《情绪之中》
编辑|LEONA
配图|来自堆糖,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